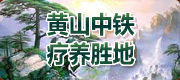徽州人概說
時間:2014-03-31 08:28:21 來源:黃山酒店huangshan hotel/黃山馨園國際大酒店/黃山中鐵旅游有限公司/中國中鐵四局黃山療
據有關專家的初步考證,古徽州到三國時候,在這塊土地上棲息的居民已有六個方面的來源。第一部分是早在秦以前就生息在這里的土著居民,禹以前屬三苗族,禹以后屬左越族;第二部分是秦始皇時徙入的“大越徙民”;第三部分是秦末吳芮部將所率后來滯留徽州的“百粵之兵”以及漢將陳嬰擁兵漸地滯留于徽的漢兵,第四部分是春秋戰國、楚漢相爭、中原戰亂,舉家遷徽的北方居民,如方弘家族由河南遷歙東,汪文和家族安家于歙等等;第五部分是為逃避賦役陸續流徙來徽州的中原居民;第六部分是留戀徽州大好山水,官于此遂家于此,或游歷至此而居此,像西漢新安太守舒許等等。這些古徽居民,既有本地原始土著山民,又有北宋的漢族、南邊的閩粵人;既有功封遷居的公侯太守,也有逃亡流落的平民百姓。漢越二族互相交融,富人中有漢越統治者,窮人中有漢越勞動人民。在歷史上人們所稱的“徽州山越人”,實際上是指:主要由當地土著、北遷南移的漢族閩粵越族農民組成的以武力反抗地主貴族和統治階級的山寨集團。當時歙縣金奇和毛甘屯駐安勒山和烏聊山,就是其代表。
經過三國時候的吳國“賀齊討黟歙”、諸葛恪“討平山越”,隨著封建政權治理的加強,徽地居民“依山阻險,不納王租”的情況逐漸改變,漢越融合同化進一步加強。因歷次戰亂等原因由中原等地大量徙入的士族官宦百姓,不僅帶來了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而且帶來了儒學文化。先后徙入徽州的程、汪、方等諸多族姓士民,在徽地聚族而居,蔚然而成“一姓也而千丁聚居,一杯也而千年永守,一世系也而千派莫紊”的宗族社會,實行極為嚴格的佃仆制,宗族內“辨別上中下等甚嚴”。所役屬佃仆世代為仆,即使這種佃仆富有的和做了小官的,身份仍然是仆,和主的門第有別,不可通婚。宗族內的富人和窮人則有血緣之溫情脈脈的面紗維系,“值歲時吉兇大事,不論貴賤貧富,集眾子孫”同在宗祠備牲醴祭祀,譜系昭穆,凜然有秩。而族內為仆者則“數世不更其名,一投門下,終身聽役,即生子女,一任主為婚配”。有專家考證,徽州佃仆制的勞役婚“贅婿”,有的長達22年,在中外贅婿勞役婚資料中,期限之長亦屬罕見。
徽州群山阻隔,早先山民保捍尚武,刀耕山伐,被稱為“蠻越”,據記載漢建武(公元30年)時太守李忠即針對“丹陽越俗不好學”,開始興學校進行教化,習禮容,傳嫁娶禮義之儀,三國吳太子鴻也曾教民習文,加上移民的大徙入,此后俗益向文雅。宋代程朱集理學之大成,完成了中華民族文化史上的一次歷史性的理性超越。程朱桑梓的徽州人,儒風獨茂,為士者多明義理,士大夫多尚高行奇節,在朝在外,多所建樹,自唐宋以來,卓行炳文,代不乏人,宋興則名臣輩出,多為御史諫官,不少名臣,剛直清廉,處魏闕則憂其民,在江湖則憂其君。
特殊的地理環境和特定的時代,又在徽州這塊土地上造就了一代儒商的徽商,他們不甘窮困,開拓進取,賈而好儒,創造了徽州物質和文化的歷史輝煌。
總之,走過了“山越”、“新安”、“徽州”幾個歷史時代的徽州人,作為中華民族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勤勞勇敢,聰明智慧,我們民族的各種美好品德和文化特性,在徽州人身上都有生動的、富有特色的體現。
徽州人尚儒崇文,居家為儉嗇而務蓄積,勤儉甲天下。農耕節用資源,養雞產卵,天人合一,保護生態。經商以義為利,誠信無欺,重人文理性追求。做工講精益求精,善發明創造,以質取勝。
徽州人重土著,進退出處講葉落歸根。置身社會樂善好施、濟困扶危,人際交往忠誠寬厚,克己待人。自身修養講吃虧是福,退一步想,知足常樂,不為己甚,以耕讀為本,甘恬退,敦愿讓,居易以位命。
徽州人慣于在入世中出世,既力求為社會效力,又淡泊名利,甘于寒素,善忍饑耐寒做“徽駱駝”。徽州人有山越先民遺存的質樸,東晉移民殘存的隱逸和耕讀心態,南宋移民留傳的藝術情趣生活追求,有玄學影響的善于思考、理學熏陶的集納精神,也有樸學訓練的嚴謹科學精神。鄉諺所謂“黟縣蛤蟆歙縣狗、祁門猴猻翻跟斗,休寧蛇、婺源龍,一犁到磅績溪牛”就是真實的寫照。 (信息來源:黃山途馬網)
經過三國時候的吳國“賀齊討黟歙”、諸葛恪“討平山越”,隨著封建政權治理的加強,徽地居民“依山阻險,不納王租”的情況逐漸改變,漢越融合同化進一步加強。因歷次戰亂等原因由中原等地大量徙入的士族官宦百姓,不僅帶來了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而且帶來了儒學文化。先后徙入徽州的程、汪、方等諸多族姓士民,在徽地聚族而居,蔚然而成“一姓也而千丁聚居,一杯也而千年永守,一世系也而千派莫紊”的宗族社會,實行極為嚴格的佃仆制,宗族內“辨別上中下等甚嚴”。所役屬佃仆世代為仆,即使這種佃仆富有的和做了小官的,身份仍然是仆,和主的門第有別,不可通婚。宗族內的富人和窮人則有血緣之溫情脈脈的面紗維系,“值歲時吉兇大事,不論貴賤貧富,集眾子孫”同在宗祠備牲醴祭祀,譜系昭穆,凜然有秩。而族內為仆者則“數世不更其名,一投門下,終身聽役,即生子女,一任主為婚配”。有專家考證,徽州佃仆制的勞役婚“贅婿”,有的長達22年,在中外贅婿勞役婚資料中,期限之長亦屬罕見。
徽州群山阻隔,早先山民保捍尚武,刀耕山伐,被稱為“蠻越”,據記載漢建武(公元30年)時太守李忠即針對“丹陽越俗不好學”,開始興學校進行教化,習禮容,傳嫁娶禮義之儀,三國吳太子鴻也曾教民習文,加上移民的大徙入,此后俗益向文雅。宋代程朱集理學之大成,完成了中華民族文化史上的一次歷史性的理性超越。程朱桑梓的徽州人,儒風獨茂,為士者多明義理,士大夫多尚高行奇節,在朝在外,多所建樹,自唐宋以來,卓行炳文,代不乏人,宋興則名臣輩出,多為御史諫官,不少名臣,剛直清廉,處魏闕則憂其民,在江湖則憂其君。
特殊的地理環境和特定的時代,又在徽州這塊土地上造就了一代儒商的徽商,他們不甘窮困,開拓進取,賈而好儒,創造了徽州物質和文化的歷史輝煌。
總之,走過了“山越”、“新安”、“徽州”幾個歷史時代的徽州人,作為中華民族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勤勞勇敢,聰明智慧,我們民族的各種美好品德和文化特性,在徽州人身上都有生動的、富有特色的體現。
徽州人尚儒崇文,居家為儉嗇而務蓄積,勤儉甲天下。農耕節用資源,養雞產卵,天人合一,保護生態。經商以義為利,誠信無欺,重人文理性追求。做工講精益求精,善發明創造,以質取勝。
徽州人重土著,進退出處講葉落歸根。置身社會樂善好施、濟困扶危,人際交往忠誠寬厚,克己待人。自身修養講吃虧是福,退一步想,知足常樂,不為己甚,以耕讀為本,甘恬退,敦愿讓,居易以位命。
徽州人慣于在入世中出世,既力求為社會效力,又淡泊名利,甘于寒素,善忍饑耐寒做“徽駱駝”。徽州人有山越先民遺存的質樸,東晉移民殘存的隱逸和耕讀心態,南宋移民留傳的藝術情趣生活追求,有玄學影響的善于思考、理學熏陶的集納精神,也有樸學訓練的嚴謹科學精神。鄉諺所謂“黟縣蛤蟆歙縣狗、祁門猴猻翻跟斗,休寧蛇、婺源龍,一犁到磅績溪牛”就是真實的寫照。 (信息來源:黃山途馬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