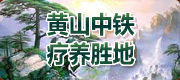徽州宗祠也可稱之為徽州祠堂。它不僅是祭祀祖宗或先賢的廟堂,而且是村落宗族財勢和實力的“象征”。村中部落的生活, 宗族的繁衍、發展和興衰,村
落布局結構均與祠堂相關。可以說一個村落宗祠的數量、規模和氣勢折射出這個宗族“煙火”的衰旺。
徽州現存祠堂最早的建于明弘治年間,至清代則多不勝舉。其大體分為總祠、分祠和家廟。總祠,作為當時重要的公共建筑,一般多置于村鎮兩端、傍山或有坡度的地方,氣勢恢宏、莊嚴氣派,少則二進, 多則四、五進,建筑依地形漸次高起,主體建筑置殿后,頗富變化。單面為中軸線上兩個或多個三合院相套而成, 民居簇擁,牌坊映照。支祠平面多為四合院式。而家廟是宗祠的一種特例,一般是官宦人家在家宅處所所建的祠堂。一般較大的村鎮,如歙縣許村、昌溪,總祠與支祠在12個以上。
如此璀璨奪目的徽州祠堂和其豐富的宗祠祭祀內容成了徽文化的活化石,形成獨樹一幟的宗祠文化。那么,作為宗祠文化發源載體的徽州宗祠是如何形成和發展的?它對徽州宗祠文化的形成發展有何作用呢?
第一、徽州祠堂的出現源于“聚族而居”。
聚族而居是維護封建宗法的需要,也是徽州宗法建制的重要表現之一。清人趙吉士《寄園寄所寄》中這樣描寫道: “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絕無一姓攙入者,其風最為近古。出入齒讓,姓各有宗祠統之,歲時伏臘,一九村中千丁皆集,祭用來子家禮,彬彬合度。父老嘗謂,新安有數種風俗,勝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動一掛一杯;千年之放,未嘗散處;千載譜系,絲毫不紊。主仆之嚴,數十世不改,而宵小不敢肆焉。”陳去病在《五石脂)一書中也說:“徽州多大姓, 莫不聚族而居。” 民國《歙縣志•風俗》還指出: “邑俗重宗法,聚族而居,每村一姓或數族,姓各有祠,分派別復祠。”徽州一帶以姓氏為基礎劃地聚居,一村一姓現象相當普遍,而且世代相沿,根深蒂固。如古歙篁墩為程氏世居,棠樾為鮑氏世居,唐模為許氏世居,江村為江氏世居,潭渡為黃氏世居;黟縣西遞為胡氏世居,屏山為舒氏世居; 績溪西關為章氏世居,上莊為胡氏世居等。 “吾邑萬山中,風俗最近古。村墟藹想望,往往聚族處。”從歙縣棠樾鮑氏宣忠堂支譜的這首五言絕句中可以看出微州祠堂最早出現與徽州“聚族而居”的原始風俗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徽州崇山峻嶺,人煙稀少,地處偏僻。何能“聚族而居”?筆者認為徽州歷史上中原大族的三次大遷徙是“聚族而居”的直接原因。民國《歙縣志》載: 邑中各姓以程、汪最古,族亦最繁,忠壯,越國公之遺澤長矣。其余各大族,半皆由北遷南。略興其時,則晉,宋兩南渡及唐末避黃巢之亂,此三朝為最盛。
造成北族南遷的第一次大遷徙是在兩晉之時的“永嘉之亂”,大批中原士族為避戰亂而被迫輾轉南遷,選擇了歷來兵燹很少, 山清水秀的徽州。從地理形勢來看,徽州確實是聚族安居的理想境地。 “東有大鄣山之固,西有浙嶺之塞,南有江灘之險,北有黃山之跪,即山為城,溪為隍”, 此次大遷徙有鮑、余、俞、黃等十族,以歙縣篁墩為主居地,環繞分散,聚族而居。
第二次中原大遷徙發生在唐代“安史之亂”和“黃巢起義”的連年戰亂,中原一帶士族紛紛南逃。遷居徽州有三十一氏族之多。至今在花山謎窟附近的篁墩流傳這一傳說:即黃巢義軍所到之處追殺中原的皇親貴戚的士族,于是族人紛紛逃往篁墩。取名為“黃墩”,黃巢軍見村名為“黃”,便以為與 “黃巢”家族有緣停止了殺戳。雖然系野史流傳,但花山謎窟的“屯兵”說已指明了其中的端倪。
第三次遷徙在兩宋的“靖康之亂” 時的宋室南遷, 中原士族以及徽州鄰近一些地方的大族入居徽州,約有十五族,以韓姓為例“宋淳熙間,天下苦于金胡之亂,朝遷暮徙, 當時民在北地者咸以江南為樂土, 實 (韓實) 由父宦邸道經休邑,見微于萬山,休邑人煙輳集,無異京華,乃留于城北居之。歷宋乾道,開禧間, 日惟遠、曰惟道,業盛家肥,人以韓家巷為名。”
其實,中原氏族的遷徙追根問源于漢代,歙人方回記載: “儲,字圣公,祖綻,本河南人,漢大司馬長史,以王莽亂,‘避地江左,遂為丹陽郡人,家歙縣之東鄉。”丹陽,即現在的宣城,歙縣此時屬丹陽郡管轄。三次大遷徙的結束,使中原的皇親貴戚的土族入落傲州,’聚族而居形成了一個個以族姓命名的村落,包括宗族鄉黨、佃客、部曲等龐大的家族體系。他們一方面有保持原有望族名門的社會心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增強土風民俗和適應性。為了有別于他族,加強聚族而.居的內部管理體系和抵御外部沖擊的防備機制,強化宗族的認同感和凝聚力,建立一套等級森嚴、排列有序、行之有效的族規家法為主要內容的宗法制度來統領。氏族和實行村落自治是族人首要選擇。這樣,制定族規家法、修訂族譜、祭祀祖先,強化族人的經濟勢力和統治地位成了宗族文化建制的重要部分。氣勢恢宏的宗族祠堂作為同族疑心聚力的神圣“殿堂”由此應運而生。
第二、微州宗祠的建制和歷史演變
從古徽州現存的宗祠遺跡遺址看,徽州宗祠的功能與其他地方的宗祠一樣也是為了祭祀祖先,昭示后人,振興宗族,凝聚人心。然而早期祭祀之地是“壇”、 “廟”。忠壯公程靈冼卒后,“里人壇其墓下以祭,里之社與壇接,尤以公配,水旱疾癘,禱之即應。”此處“壇”即土筑的高臺; “社”即社屋.社屋緣社(土地神) 而建。 由于祭壇與社屋相鄰,雖兩者建筑式樣迥然不同,但祭壇由此被賦予“社神”那種“禱之即應”的功能。 •
到了南宋寧宗嘉定年間 (公元 1208—1224年),程氏后裔程王必等在墓旁買地建廟,朝廷賜廟額“世忠”,納入祀典,程王必于是“倡休、歙族人捐田入篁墩廟,每歲合一鄉六社之人迎神至漢口祀。”由祭壇到廟的變化,使祭祀規格上升為“神”。 “世忠廟”位于歙縣篁墩,四鄉八鄰程姓族人舉行祭祀大禮,必先到篁墩從廟沖請神,后再在各居住地建廟以祀。
以廟供奉“神”與以宗法制度為核心的祠堂不同。祠堂是以宗族為單一群體,適合于族人里人的平民,具有濃厚的平民化色彩。從設置的位置看,徽州祠堂一般置于村落的風水之地,在村的中央和高處。而社屋、神廟和墓葬一樣,在村口和村外。此外“行祠”的出現使祭祖形式大眾化、 多樣化和崇“神”化。
以徽州程、汪兩氏為例。微州程姓始遷祖是程靈冼的祖輩程元譚,西晉末年永嘉之亂時,程元譚起兵鎮守新安,因•有功于民,詔賜田宅于歙,因家焉”。程元譚由此成為徽州程姓的始遷祖。徽州汪姓的始遷祖是汪文和。東漢末年時,汪文和為龍驤將軍, “避地始遷新安,子孫遂為新安望族•,汪文和由此成徽州汪姓的始遷祖,后人建•汪王廟”以祀。’雖然程元譚和汪文和為微州程、汪兩姓始遷祖。但其膏孫.大多祭祀的是趙國公汪華和忠壯公程靈冼。兜其因是因為世家大族遠遷徽州異地后,為了區別于當地的山越苗裔,同時也為顯赫族人的政治地位的優越,把在微州立下赫赫功名的先祖作為徽州始祖拜謁可以昭示族人并給自己的族人帶來名望。在這種社會大眾化心理驅使下,原本屬于社屋才有的•地域神”漸漸疊印到“墓祠”先祖身上,成為大眾禱告的偶像。